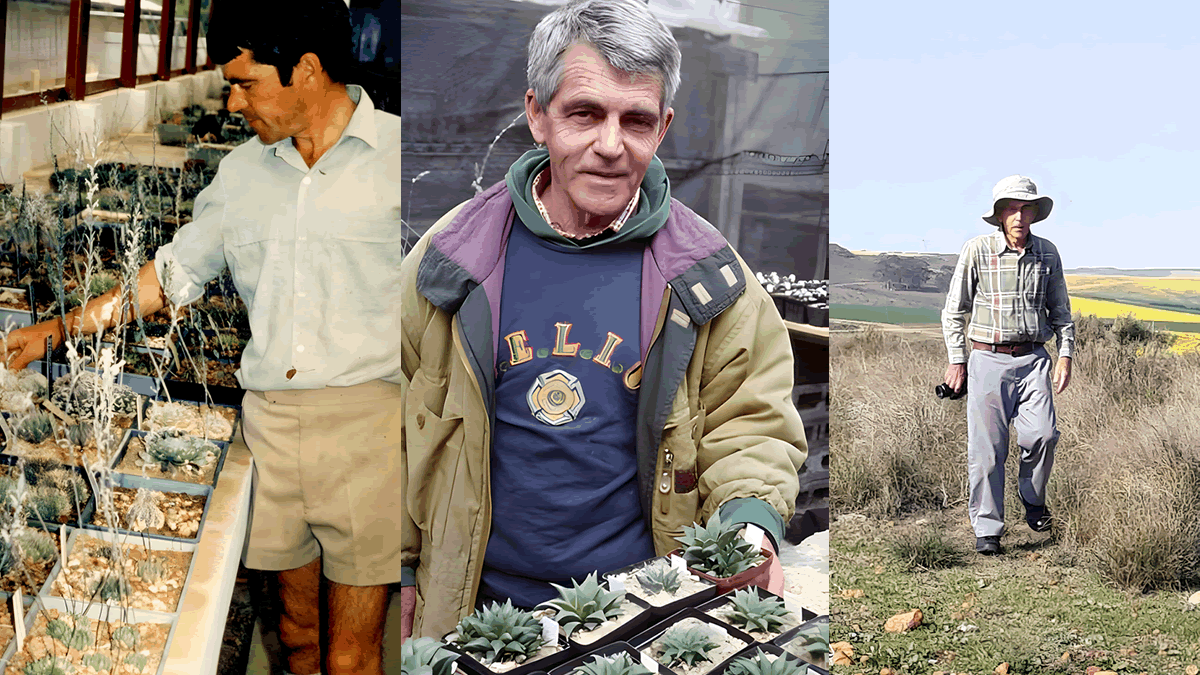布鲁斯·拜尔(Bruce Bayer)是瓦苇属(Haworthia)的终极权威。他在探索瓦苇属原生地的投入时间,无人能及,未来也恐难有人超越。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,他撰写了众多文章,并出版了多部著作,包括《瓦苇属手册》(1976年)、《新瓦苇属手册》(1982年)、《瓦苇属再探:属的修订》(1999年),以及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的多达11卷的《瓦苇属更新》。毋庸置疑,《瓦苇属再探》是一部经典之作,但布鲁斯并未止步,他持续不懈地进行野外研究,揭示了这一属的复杂性,以及物种界定和分类编码应用于这一多变科属时所面临的难题。尽管他的某些观点在科学界显得过于激进,且其意见仍饱受争议,但他拥有超过60年的经验、研究、野外考察和积累的知识作为支撑。
布鲁斯一生都在追寻真理。这一追寻既是身体上的,也是精神上的,是他深入了解瓦苇属的动力。鲜有人能理解他的追寻。简而言之,这是一项了解并热爱上帝、进而热爱整个造物世界的使命。布鲁斯深知自己的使命远非完美,但他从未偏离自己的崇高理想。身体与精神的追寻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。
在布鲁斯的旅程中,他激励、鼓励并支持了许多人。各行各业的人通过他了解并爱上了瓦苇属和南非的原野。得益于全国各地慷慨的土地所有者和农民,他得以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观察它们,其中许多人成为了他的挚友。
布鲁斯在脸书上的最后一条帖子是:“乘着歌声之翼,我将带你前往,那迷人的仙境。”他热切地希望回到那迷人的仙境。无疑,瓦苇属的谜团和我们造物主的其他奥秘将在那里得到解答。他终于可以安息了。这是他应得的。
——//——
对布鲁斯·拜尔(MBB)的敬意
德里克·特里布尔(Derek Tribble)
布鲁斯·拜尔对我们很好。1977年,我们手持一张免费的旅游地图,在南非四处寻找多肉植物,却不知该从何做起!当我们造访伍斯特的卡鲁植物园(KBG)时,受到了热情的欢迎,并获准拍照留念,记录下那里丰富的私人瓦苇属收藏。这里有在英国从未见过的瓦苇属植物:H. wittebergensis、woolleyi和springbokvlakensis。1980年及以后,我独自返回,并有幸入住简朴的客房。随后拍摄的照片中包括了令人惊叹的新品种,如H. bruynsii、pubescens和koelmaniorum,这些照片在早期的瓦苇属协会大会上引起了极大兴趣。
布鲁斯在瓦苇属分类学上进行了公开而深入的探索,随着多年思考的演变,他反复撰写了大量详细文章。他试图解决林奈双名制与野外复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性。早期著作中,他提到了杂交群,但尽管认识到需要更好地理解进化过程,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术语。(近年来,通过比较核DNA与质体DNA的结果,研究方法才得以发展。)或许早期决定不承认亚属分类,导致他后来将新发现划分为多个物种,其中许多在后来又被合并。他后期的一些著作探讨了分类哲学,对我来说已难以理解。他最令人难忘的将是与科布斯·文特(Kobus Venter)、科蒂·雷蒂夫(Kotie Retief)和史蒂文·哈默(Steven Hammer)合作的优秀著作《瓦苇属再探》,我在《BCSJ》17:4(1999年)第198页上给予了热情评价。随着彩色印刷的普及,他后期的出版物通过照片详细记录了瓦苇属在野外的自然变异,或许比南非任何其他植物属都要详尽。
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,其理论远超分类学范畴。尽管发表在流行杂志上,但他的文章《开普花卉与卡鲁——冬季雨林生物群与芬博斯生物群!》(《Veld & Flora》,第70卷第1期,1984年)对后来被确认为独特的多肉卡鲁生物群(区别于夏季降雨的纳马-卡鲁)的认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布鲁斯鼓励在卡鲁植物园进行多肉植物的科学研究,但他的国家生物研究所(NBI)管理者并不认同这一愿景,他们希望科学研究在开普敦的科斯滕博什进行,并强调伍斯特的教育功能。最终,双方分道扬镳,布鲁斯在18年后离开了卡鲁植物园,但继续在自己的时间里种植和研究瓦苇属。我们对瓦苇属的当前了解,布鲁斯比任何人都贡献更大,我遗憾他从未接受邀请在英国发表演讲。
——//——
漫步天堂花园
史蒂文·哈默(Steven Hammer)
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5月,我在卡鲁植物园担任志愿者。这一非正式、看似不可思议且令人愉快的安排,是由植物园馆长马丁·布鲁斯·拜尔(即MBB)提出的,他在总部为我疏通了关系。这个总部,也被称为科斯滕博什,不知怎的解决了我的非财政雇佣合法性问题。助理馆长约翰·温特博士(Dr. John Winter)甚至给了我一个确认性的握手,力度之大让我意外地跌坐在他光可鉴人的地板上。我从未完全恢复平衡。
当时,科斯滕博什因其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和靠近开普敦的地理位置,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资金。但卡鲁植物园,被多肉植物的原野和相对朴素的页岩峭壁环绕,拥有自己宁静的乡村美景。最重要的是,它有MBB,它是整个植物园的核心和活力源泉。他从修剪多肉植物的工人,到与“全能的邱园”(如拉里·利奇(Larry Leach)在描述大戟属时所说)争论的室内研究人员,或检查稀有的Eriospermum块茎(波琳·佩里(Pauline Perry)的艰巨任务,因为可用的块茎太少了)的科研人员,都激发了整个植物园的活力。
我的工作很简单。我给肉锥花属(Conophytum)和瓦苇属植物浇水、繁殖和换盆,为植物园渴望数据的新电脑输入数据,引导多语种的游客,并帮助布鲁斯制作植物标本。最后一项任务工作量很大,而且往往有自己的时间表,因为布鲁斯总是想记录花朵。
瓦苇属收藏生长在老旧的黄色玻璃纤维下。
这特别适合这些植物。阳光被过滤但不过于昏暗,夏季的炎热也得到了缓解。充足的侧面通风有助于防止植物徒长和腐烂。这些植物作为南非遗传多样性的半公共展示,为它们的官方“晚餐”而歌唱,但它们主要是为了布鲁斯的沉思和分类探索、繁殖,以及纯粹的惯性而存在。
一些杰出的品种:
- 巨大的beukmanii,叶片歪斜如复活节岛的巨石,拒绝倒下;
- 光滑如镜的comptoniana,自花授粉如酵母般容易;
- 经过蛭石点缀和海藻补充的sordidas,看起来并不那么邋遢;
- 来自Kransriviermond的retusa(mutica nigra),叶片呈焦糖棕色,双层涂漆般光亮。布鲁斯非常喜欢这个收藏,以至于他让我带走一半的种子,在美国建立前沿阵地,我也这么做了;
- 由黑曜石制成的dimorphas;
- 当时的magnifica major,颜色在炭黑和雪白之间变化;
- 独自在大型石棉水泥托盘中的mutica Drew,浑身覆盖着白色斑点。
与此同时,整个收藏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:从布鲁斯最深层的角度来看,盆栽植物本质上总是令人不满意的。没有Kransrivier的Haworthia retusa就像没有Haworthia retusa的Kransrivier一样不完整且乏味!
布鲁斯拥有非凡的视觉记忆力,能够随时唤起那个地点和它的精神——这一能力非常了不起——但这并不能帮助那些植物,也不一定能帮助人们普遍理解,除非布鲁斯像他当然做的那样,在出版物中呈现这一场景。
否则,脱离数据、无根的植物已经接近栽培品种,容易陷入千种混乱。因此,布鲁斯坚持制作干燥标本——我称之为木乃伊——并对收藏中的一切进行无数次拍照,形成永久记录。
或许不如《蒙娜丽莎》那样永恒,尽管她也在开裂和褪色。与此同时,她提醒我们时间旅行的现实。
当我看着我的Haworthia retusa/mutica ex Kransriviermond ex KBG时,
我直接回到了1985年10月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也是昨天。这一切我都归功于布鲁斯。